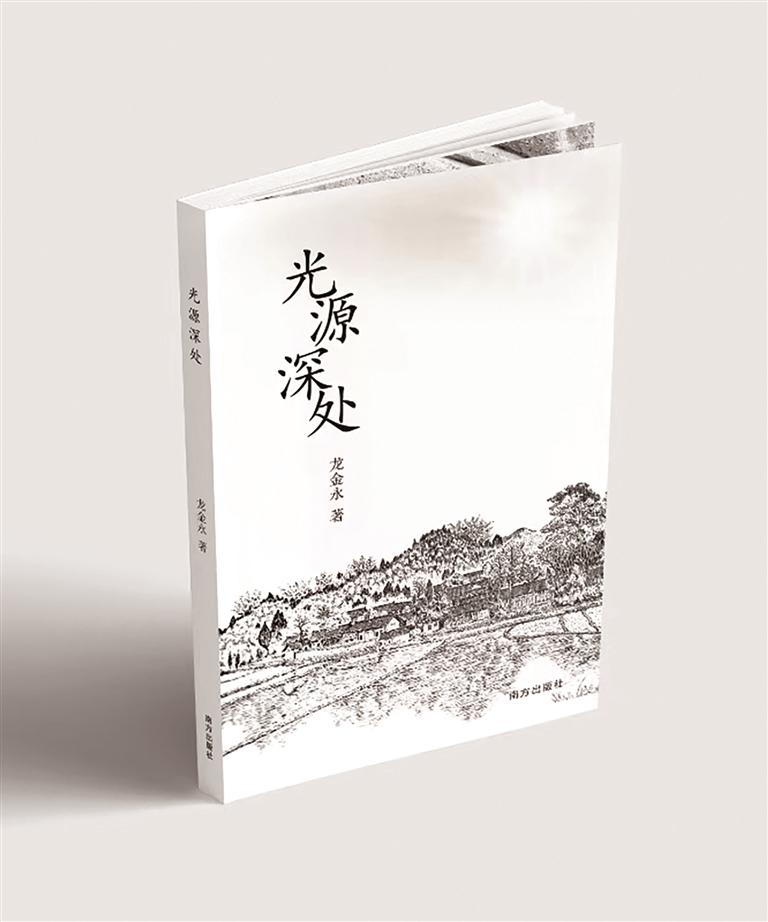杨碧薇
龙金永曾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与我有过课堂之缘。那次的课程安排很紧凑,我们在课下没有太多交流,但她的勤奋和谦逊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知道,这些年来她笔耕不辍,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果,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等重要的文学杂志,诗歌入选多种选本,还作为代表参加了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我正在阅读的《光源深处》就是她出版的诗集。这次阅读,也算是弥补了之前交流疏浅的遗憾,因为诗人的诗乃是其灵魂的写照,见诗如晤,我对这位出生于贵州松桃的苗族女诗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真诚与朴实,是《光源深处》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龙金永的诗平实易懂,叙述时兼顾简洁和流畅,既不耍花招,也不走捷径,而是始终以真情来面对文字,以此实现与读者的心灵共振。值得一提的是,她有大量的诗包裹着深层的“拙”感。我说的“拙”并非笨拙,而是一种大大方方的朴素,具有生活的质感,蕴藏着鲜活的生机,让我想到《红楼梦》里探春喜欢的那些小玩意:柳枝儿编的小篮子,竹子根儿挖的香盒,胶泥垛的风炉子……试看两例:“木瓦房,是村庄低矮的支架/稍高一点,是瓦片上的树梢/再高一点,就是两座山峰/遥相呼应的顶点了”(《我的村庄》);“火塘的右方,我不敢乱动/必须由父亲,取中柱的东西正位/用三块火砖,一片青瓦/为神灵,安一个家”(《神坐的地方》)……这种平实朴拙的面貌之于诗歌主题,不仅是内质上的契合,还是精神上的印证与放大——诗人放弃了饶舌,只用粗茶般的语言书写乡村经验,因而笔下呈现的乡村形象也带有一抹“拙”的生命力。粗茶是大多数人都能获得的物品,能随时随地给生活增添滋味,还有温度,有人间的烟火气。可以说,粗茶式语言,强化了龙金永的诗歌特质,更给这些诗加添了可靠性和亲切感。
我刚才引用的诗句亦表明:龙金永还擅长使用描述性的句子。再如“椿树下的一堆堆草垛/被抽走掏空,消瘦而凌乱”(《在村庄过冬》)、“它用篾条支撑的骨架/经过半世纪的日晒雨淋/再也接合不住/漏洞百出的棕须”(《斗笠》)等,这些描述均由细节构成,富有造型感、画面感。要注意的是,看似客观的白描里,也站立着作者的情感。描述背后首先是某种介绍的动机,也即分享的冲动——正因为对故乡充满深情,诗人才想把这片土地的一点一滴都介绍给读者。读这些诗句,仿佛身临村庄,诗人就是导游,在为读者讲解眼前的景象和乡村的民俗。随着细致的讲解与描述,一帧一帧的场景就在读者面前闪过。其次,出于敬畏感,诗人也大量地使用描述手法,而不是滥用其他修辞。试看两例:“右边那间,得铺地楼板/刷上桐油,设一方周正的火塘/备置一个三脚架/支撑鼎罐”(《神坐的地方》);“夜间,不允许在灶台上/摆放碗筷瓢盆,只能放/一盏灯和一方白豆腐/再点燃一炷香”(《母亲说》)。这两首诗里涉及的空间布置、器物摆放,以及作者的叙述口吻,是有统一的仪式感的。仪式感正源于敬畏——仪式,能替人们更好地表达敬畏之心;而人们敬畏的,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伦理秩序。
谈到这里,又涉及到新诗书写中的伦理选择问题。在现代化高速运转的今天,已定居城市多年的龙金永,依然将这本诗集的主阵地留给乡村,执着地书写乡村记忆与原乡经验。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作者的审美偏好;究其核心原因,则是作者的伦理选择,是诗人对自然原乡的长期体察,对乡村伦理的由衷认可。敬畏之心,正如她在《舂谷》中所示,“面对它们,/我不敢再使用金光灿灿的修辞了”。正因有坚实的乡村伦理兜底,在龙金永的诗里,我看不到个体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中产生的身份分裂感,也看不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尖锐对立。尽管《哈哈镜》也涉及到“由乡野带入城市”的主题,但作者的态度并非狭隘的乡村思维,更非对城市文明的偏颇审判,而是承认这一历史进程及大进程之下个体命运的复杂性、多元性与可能性:“把砂砾和金子都装进来/再用一生慢慢锻打”。如果说《哈哈镜》只是侧面滑行,那么《在河里捉鱼摸虾》一诗,就更为直接、清晰地展现了作者的态度。“最难忘那时光的宽容仁爱”,早年乡村生活是龙金永一生的情感养料和力量之源,襄助她顺利地完成从童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中的诸多转化。如果“不慎滑落山谷”,那就“如一个走失的孩子/哭喊了一阵,又继续/在河岸丢石子/在河里捉鱼摸虾”。乡村经验的滋养,让龙金永能在生活与身份的转捩中保持内心的平衡,找准自身的定位,并维护好一个属于个体的诗歌小世界。“而我这一生,只学会用一支/不轻不重的笔,把几个字词/堆码成半亩贫瘠的土地”(《劳作》),“所以我的身体/只有植物的馨香/动物的腿脚/没有一点铜臭味”(《这里不产黄金》),“我愿意作那/柔软的部分,在黄昏/与它们的伤口一点一点咬合”(《石板路》),这些诗充满了乡土伦理孕育出的秩序感与分寸感,不卑不亢,克制,健康,明朗。
由此,龙金永在诗里呈现出一个独特的个人形象——从乡村到城市的“山中人”形象。一方面,诗里的主体“我”是不折不扣的山中人,对山中生活十分熟悉,打谷、晒谷、打笋,样样在行,写苗药、苗绣、蒸桶,有模有样;“我”保持了山中人的底色,真诚朴实,还有认准了理就无所保留地热情:“以竹筒倒豆之势/给你,一颗不留”(《山中人》)。另一方面,这个山中人也有开放的视野,不拒绝成长,不自我设限。离开故乡,她也能看到城市的诗意,“在二十层楼与一轮落日相对/……独享一片大而虚无的空间”(《与一轮落日相对》);能在陌生的地方享受风景,“是我用凡肤俗体/向四个山峰的问候/是我用驳杂的私欲/对纯洁的絮语”(《四姑娘山》)。有意思的是,从故乡的山到四姑娘山、巴郎山、横断山,对山的注视,一次次催发出龙金永的诗情。我大胆猜想,如果没有故乡的山,没有自小就具备的对山的敏锐观察,龙金永恐怕也不会在陌生的风景里收获如此丰厚的审美体验吧。
最后,我们再回到目录的编排上,来一窥诗人的巧思。诗集名为《光源深处》,全书的五个小辑也都与光学、视觉有关,分别是《聚焦》《映照》《回望》《折射》《色散》。这真是一位对光充满执着,也能用心用情感受光的诗人!我想,无论是用哪一种观看方式,无论看到了什么,龙金永都始终热爱光芒。如同她在诗里的期冀,“我总是走进光的深处/攫取它的一小撮/作为我入库的半两黄金”(《光》),在此我也祝福她,能够不断进入光的深处,去捕捉生命的灵光,记录下诗的感动。
(作者系诗人,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