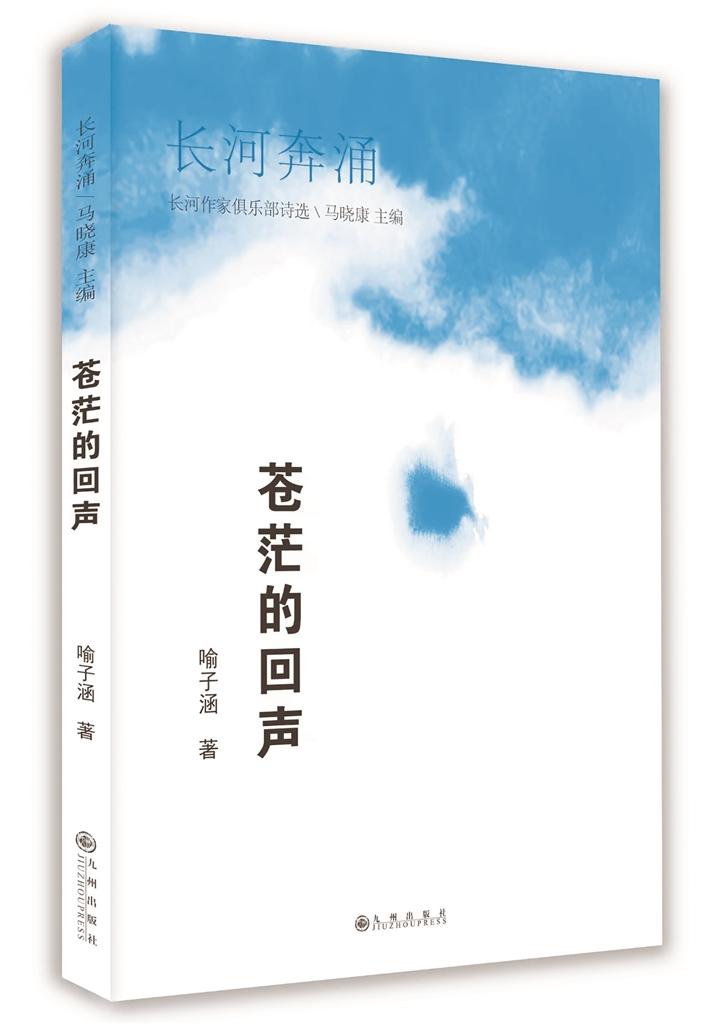灵焚
喻子涵是当代知名的散文诗人,他的作品在语言与思想上达到了深邃的契合,情感与节奏张弛有度,审美与意象从容自然,诸多作品的语言,看似随手拈来却能让思想在存在与揭示之间充满张力,从而点石成金,让人抵达豁然开悟的哲思之境,不着痕迹地呈现出散文诗作为一种“思想诗”的重要本质。正如所知,关于散文诗有一种认识,那就是其属于诗歌文学中的一种“思想诗”,思想深度与高度决定了散文诗作为一种诗歌文学体裁存在的独立性意义。虽然散文诗的“美文性”被许多人所认可甚至被一些人所强调,但那只是其表象而非本质,其本质必须是“思想性”。如果散文诗不能揭示人所处的某个时代认识世界的前沿思想与揭示人的存在的独特而前卫的审美,那其作为诗歌文学存在必然会被分行诗所歧视,同时也会被其散文性外观所遮蔽,成为可有可无的不入流存在。令人欣慰的是,喻子涵的散文诗让我们看到了其诗性与思想性的高度融合,既具有美文、韵味,又呈现浓密而深邃的哲思,许多作品看似日常语言的平实叙事,却让人抵达余味无穷的审美秘境。评论界概括其作品具有“低温沸腾”的审美特质,多少应源于此中况味所致。
喻子涵的散文诗,让我再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与认识所具有的合理性。笔者关注喻子涵的散文诗创作已有多年,对于其作品还是比较熟悉的,纵观他的散文诗创作之路,明显存在着这种审美与思想的成长与变化的轨迹。就《苍茫的回声》这本厚重的作品集而言,这种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诗歌作者的创作之路,并非都能越写越好、年龄越大佳作越多,许多人更是恰恰相反,这才有古人所谓的“江郎才尽”之说。但散文诗不同,好的作者往往是年龄越大,审美与思想越成熟,其作品写得越好,到了晚年更是佳作频出,比如耿林莽前辈在耄耋之年,仍深耕创作佳境,成为我国当代散文诗坛的审美佳话有目共睹。只要对比《苍茫的回声》上、中、下三卷中所有作品的写作时间不难发现,喻子涵的散文诗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渐入佳境的审美气象。其中最早的作品《登梵岳遇佛光》,初稿写于1993年5月,而最后的作品是《闪烁的微尘》断章中的某一节,完成于2023年12月。在这部作品集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审美境界、诗性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乖离,情感、语言与审美对象并不契合的违和感,存在着“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写得不错,比如该作品集的开篇《贺兰山岩画》(3章),通过把审美对象以“你”对象化,让审视者“我”与其平等相遇,把二者之间的关系拉近,如情侣间深情对视,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很自然地交换着各自的心跳,让人顿感情真意切地圆融一体。但是,这种现象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也只是个别,不是全体。然而,到了2014年之后,这种创作能力的青涩感明显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其运用语言表达审美主体对于世界的认识,并进行审美呈现时逐渐显得从容不迫,作品的语言看似随手拈来,却皆能恰到好处,并往往让人产生审美的惊喜与抵达哲思的开悟,比如《中年情绪》(7章),《光芒与暗处》(10章)等“下卷”中的大多数作品,其大都创作于2017年之后,那些作品大都能给人带来阅读的惊喜。这也许与他在此之前刚完成了《汉字意象》系列作品的创作有关。
散文诗集《汉字意象》是在2013-2016年之间断断续续完成的专题作品集,这些以汉字的某个字为审美对象的诠释性呈现,此前作品中存在的叙事冗长乃至自作多情的审美强制痕迹已经消失,而是力求以自然且诗性的审美语言企及深邃的哲思,让每一个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审美灵根与现代生存的对应性意义复活。为此,在作者的2014年之后的作品中,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审美从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被编入此作品集的近年来的那些新作,这种审美从容则更臻成熟。同样是对眼前的各种事物、景象、事件、事态等审美呈现,在中、下卷中已基本上不再出现物我、事我之间的乖离感,呈现出以自我的生命律动聆听事物、事态的自性言说,敞开灵魂与世界平等对话,并从这种“对话”中不露痕迹地浮现、对应人的情感、思想与存在的境遇性体悟。此时的审美自然而然,思想浑然天成。特别是最后的创作于2017年5月-2023年12月的《闪烁的微尘》这组箴言性短章,其审美与哲思浑然天成,内蕴余韵缭绕,令人回味无穷。
喻子涵的散文诗创作之所以能够随着年龄与思想发展而不断提高,这可能源于他对于自己的创作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与对于诗歌是什么、为了什么的清醒认识。在《苍茫的回声》“后记”中,他对于自己的创作历程与审美探索作了如是概括:“在‘孤独的太阳’时期,差不多有着较为明显的文体意识,即分段式写作……没有完全遵守当时某些过于拘束的所谓‘散文诗’范本,我只是热衷于散体的诗歌写作而已,故大量运用超现实想象和现代性手法;到了‘汉字意象’阶段,明显倾向于‘诗化’写作,增加意象呈现……注重情景、细节的铺设。到了《苍茫的回声》,变化则更大,篇章结构上都是组章,格式上散体写作和诗体写作兼备,甚至还有短信或微博式的短章写作……当然,不管是哪一个时期,象征与哲理这个根基都没有丢失,语言的质感没有丢失,保证了散文诗的诗性品质。”
从上述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作者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散文诗文体表现的各种可能性,其文体意识明确,尝试各种表现手法,努力呈现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诗歌体裁的多样性特质。这里所说的“孤独的太阳”“汉字意象”,都是他在不同时期出版的作品集名称,同时也是他在该时期所探索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的一种呈现。这部《苍茫的回声》,基本上都是作者上述二著之后最新作品的结集(个别早期的草稿,也是在近期修改定稿),由此可见,这部作品集,应该是作者现阶段所抵达的审美与思想之至境的呈现。尽管作者将其以“散体”与“诗体”的不同探索时期予以区别性划分,都无法企及在《苍茫的回声》中所追求的“散体写作和诗体写作兼备”之审美与思想浑然契合的艺术高度。只要阅读全书则不难发现,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卷的《苍茫的回声》,越往后其中被收入的作品则越好,其创作时间基本都在2015年之后,乃至最后的箴言性组章《闪烁的微尘》,虽然写作时间跨度从2017年5月至2023年底,并可能属于一些“未完成”的断章式哲思,而正是这种似乎“未完成”的断章,成就了其中的审美留白与思想余韵的相得益彰,犹如欲语又止,有某种残缺之美呼出语出,成为该作品集所呈现的作者业已抵达的审美峰顶,闪烁着审美与哲思相互生成的艺术光芒。
那么,《苍茫的回声》这部作品集,究竟所揭示或者所呈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苍茫的回声》是一部厚重的作品集,可诠释的问题是多元的。从我阅读后的整体感受而言,这部作品集的审美与思想,从总体上看,似乎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指向一个被广泛流传且悠久地困惑着人们的、可谓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之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根本追问,终极求索。对于喻子涵而言,“世界就是一堆梦幻的积木”(《梦:积木与地图》)。所以,无论他的山水行吟,还是人文习俗的审视,乃至面对社会现象、历史人物、个体生存境遇的省思等,其本质都是在确认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或象征或哲思的语言揭示这种关系,并以这种揭示来呈现作为人的审美性存在,企图确认自己“是谁?”“哪里来?”“哪里去?”的问题。而要完成这种确认,生存与世界的关系逻辑是无用的,只有在语言中寻找才是有效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散文诗人、散文诗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