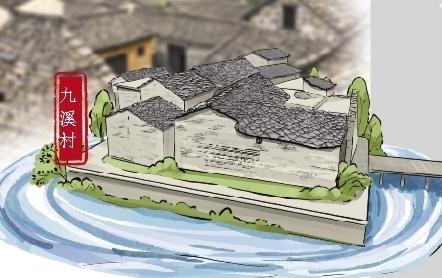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散布贵州的屯堡古建
2006年,建筑设计师越剑带领他的学生,租下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本寨村最大的碉楼,开始了师生的第一次乡村修缮实践。他在碉楼里成立了工作室,编著了讲述屯堡建筑的《河里的石头滚上坡》一书。书中介绍,本寨有7个碉楼,每个碉楼是一个防御单元。明清两朝汉族工匠把家乡的传统带到贵州,由江南的砖木结构变为石木结构,把平原地区轴线院落关系改为贵州山地的防御组团体系,形成了屯堡民居聚落最有特点的文化景观。
师生们租下了王尚义家碉楼,该碉楼为“歇山顶”制式,有四层楼,由于年久失修已荒废。越剑请屯堡本地的金家匠师带领学生加固屋顶,安装窗户,增加麻绳栏杆和灯光照明等。修缮中他们发现因为民居内外粉饰的石灰保护,石墙竟然没有受到山间潮气的侵蚀。后来越剑把石灰样品送到同济大学石灰实验室化验,发现安顺屯堡地区的石灰都是镁质石灰,后期硬度比石头还硬。越剑说:“屯堡石头化成灰来保护石头,让我们600多年后还能和这些屹立不倒的石头建筑相遇。”
屹立不倒的屯堡建筑,散布于贵州多处。有的在设计师手中重焕新生,有的在从古至今的生活中从未缺席。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罕见的有中轴线的村子。这条中轴线由南向北,经屯口—瓮城—汪公殿—大佛殿—关圣殿—练武场—鲍氏宗祠—振威将军陵园贯穿,强调中轴对称和主次分明。古时的军事防御功能,在鲍家屯的内、外八阵的布局上一目了然。几百幢坚固的石头房屋和巷道构成的“内八阵”,包括青龙阵、白虎阵、长蛇阵、雄狮阵、玄武阵、金鱼阵、鹿角阵、火牛阵,一溜名字听起来就让外来者瑟瑟发抖,仿佛瞬间已经深陷“迷魂阵”;“外八阵”则是利用寨墙外四周的山峰和河道,以石墙、碉堡、岩石、壕沟和河沟构筑成的八道外围防御阵地——又要安全地活着,又要安适地生活,屯堡人做到了。
黔东南州锦屏县的隆里古城,是明洪武年间所建的龙里守御千户所,从中原和江南等地千里而来的60户“军人家庭”成为首批入驻者。今天在隆里古城溜达,年轻人会觉得这里很适合玩剧本杀,只要穿上一身古装就能演穿越剧——至今保存的“三街六巷九院子”,是当初军事移民们中原家园的“平替”;当然还适合玩一回古堡版的密室逃脱——将军事防御理念贯穿到建筑设计中来的村寨,防御体系完备,设计周密。
这座军屯定位的城堡,在当时的建设条件下做到了极致:城墙高筑,街巷设置错综复杂,街巷交接处都没有设计成“十”字而是采用“丁”字形(《隆里所村志》上说,这是因为“十”与“失”同音,不吉利。而“丁”则寓意人丁兴旺,打起仗来不损一兵一卒);北门大街还有意不与东西主街相通,一旦发生战事,可用于转移人员;居民后院均设有后门,户户联通;城门有内外两道,并架设可收放的吊桥,跨越城壕通往城外;至于城外,原来也有机关,在周围的城郊山坡上,还设有军事营盘……如此步步为营的设计,要是在其间玩一场“古堡逃脱”的游戏,要多强大的玩家才能完美逃脱呀。
莹白石头建造的家园
石墙石柱石门洞,石磨石碾石板路。屯堡村落就是石头的世界。如果你爬上云鹫山顶俯瞰,你甚至会觉得身下云峰八寨之一的云山屯那些密密的,用一方方切割得整整齐齐的石板做的屋顶,就像一本本石头做的书,让你有翻开细读的冲动。
屯堡村寨最为集中的安顺,就是一座石头城。安顺位于喀斯特山区,石头多、土层薄,烧砖造屋并不现实,石头就成了最好的建材。但安顺的石头又比一般的石灰岩更富含镁质,不仅更加坚固,颜色也有洁白莹润的质地。贵州著名作家戴明贤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安顺》的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安顺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这“莹白”,并非文学修辞。
习惯了砖木建筑的屯堡人祖先来到石材丰富的贵州之后,因地制宜,开始利用石材建造家园。石头不仅是城墙、房屋、街道、水渠等建筑材料,就连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器物,比如碾、磨、水缸等等也是石头雕凿。坚硬又莹白的石头,在屯堡建筑和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600多年屯堡的家国风云,也仿佛一部读不尽的“石头记”。
屯堡人很善于和自然环境“打成一片”,除了就地取材运用石头,他们在村寨的选址上也总能找到“风水宝地”。每年春天,鲍家屯村口那一大片宽阔平整的油菜花地和潺潺河水,吸引了很多人前去打卡。《黄帝宅经》里“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的理念,在鲍家屯以及屯堡很多村寨得到落实。后有靠山,前带流水,侧有护山,远有秀峰,住基宽坦,水口紧锁的鲍家屯,与环境融为一体,建筑布局绝佳,同时还承载并沉淀着600多年中“大时代里的小人物”的命运和情感。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俨然已是件令人咀嚼和感叹不尽的大地艺术。
武汉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博士耿虹在其《安顺屯堡建筑环境景观研究》一文中说,屯堡建筑“自觉选择了个体建筑在山水环境中的扎根与生长方式”,有时还通过一些地标性建筑的有意味的安排,如屯墙、门楼、山顶等,“构成中国式的建筑个体与自然环境融合的理想画图。”
石头成全了屯堡的封闭性和防御性,然而这种自成一体、隔绝周边并不是这些石头村寨的全部,天龙屯堡就是作为“通道”的遗存。据中国明史学会屯堡研究分会副会长吕燕平介绍,天龙屯堡不是明代卫所下辖的屯军村落,它由驿站“饭笼铺”发展而来,早在元代就已经是驿道上的重要站点。
驿道,是天龙屯堡的主轴,串联起为纪念随明军入黔的四位始祖而修建的“四公碑”、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屋“九道坎”,还有由民居开辟为地戏表演场地的“演武堂”,今天的游客甚至还能在古驿站里喝上一碗“驿茶”。而围绕天台山的古城墙、加工兵器的“打铁坑”、烟堆山上的烽火台,则体现着武备之风。作为“通道”的它,依旧是明代军事防御体系的一环。
传统审美中的乡愁
离乡背井的屯堡先祖用贵州石头建造了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家园。但石头只是主要建材,建造新家园的屯堡人同时又在建筑的各个环节和细节之上,留下自己所熟悉的江南民居的印记。他们像在长途跋涉过程中留下记号的远行者,在建筑上为自己“从哪里来”标注答案。
江南民居的卷棚外廊与抬梁式结构的结合,在屯堡公共建筑中得以延续下来;而江南建筑中常见的中轴线布局,在环境多山的屯堡不再只以南北取向,而是因地制宜地改成了东西向庭院,缓解了台地交通,有些院落形成独特的“歪门正厅”。
屯堡村寨那些“燕窝式”小四合院或三合院,面积虽小,却布局紧凑,轴线明确。江南四合院所讲究的以中轴线对称布局,按尊卑、长幼、男女、主仆的关系来安排家庭成员住所的位置,除了在屯堡建筑中有体现外,还在院落的对房或边角处增加了“农耕文化”中的牲口房。这种布局所代表的结构严谨、等级有序的中原文化内核,被包裹并延续在了“屯田制”为本底的山石堡垒之中。
对石头的运用,以及对木头的保留,让石木结构的屯堡建筑成为一个“外刚内柔”的生命。从外观来看,以石块和石板构成坚固无比的城堡,但在宅院内部,却充斥着雕花的木质家具、雕花的石柱础等家居和装饰。和粗粝的外表相比,它们简直就如同深藏不露的“细软”。
尤其是门窗,精雕细琢,图案多变。那些排列有序的点和横竖交错的线,以及点和线在具体的空间和特定的光线环境下所产生的虚实明暗的视觉影像,让家常的门窗变成了一件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尽管屯堡民居研究者耿虹认为“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也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屯堡人无法形成江南官僚士绅及文人文化那样的精致文化品格,从而使得屯堡建筑风格显得更为粗放自然”,但在屯堡建筑的内部空间中,这些来自江南的石雕和木雕工艺进行的装饰,正是融入屯堡文化基因里的江南传统审美。
坚固石头房屋固然能抵御外来侵犯,却终究难敌时间的无孔不入。老屋已老,被滚滚向前的生活渐次抛下,却又有古建保护者的努力使之获得新生,活态传承。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修复屯堡古建筑的建筑师越剑,是明代随军入黔的杭州临安越氏后人。继2006年修缮本寨碉楼,并租下使之成为自己第一个研究屯堡民居的乡村工作室之后,他又发起了“屯堡工作营”,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志愿者来到云山屯(云山坉),每年修复一座院子,迄今已逾10年。“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故事”,越剑说,而这故事尚未结束,还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