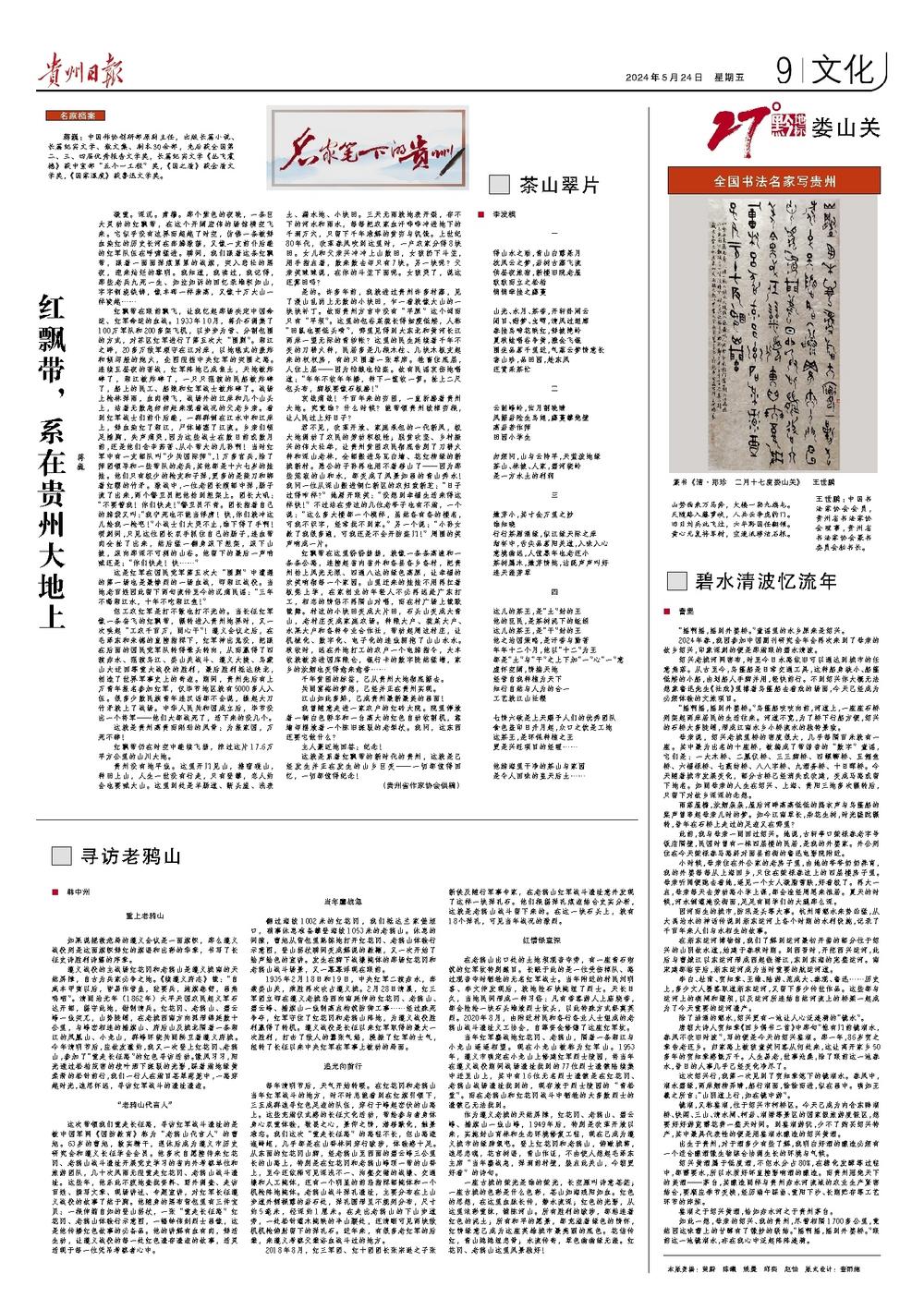■ 曹雯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童谣里的水乡原来是绍兴。
2024年春,我因参加中国副刊研究会年会再次来到了母亲的故乡绍兴,印象深刻的便是那满眼的碧水清波。
绍兴老城河网密布,时至今日水路依旧可以通达到城市的任意角落。从古至今,乌篷船是日常交通工具,这种船身狭小、船篷低矮的小船,由划船人手脚并用,轻快前行。不到绍兴你大概无法想象鲁迅先生《社戏》里撑着乌篷船去看戏的场面,今天已经成为必须体验的文旅项目。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乌篷船吱吱向前,河道上,一座座石桥则架起两岸居民的生活往来。河道不宽,为了桥下行船方便,绍兴的石桥大多陡峭,形成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独特景致。
母亲说,绍兴老城里桥的密度很大,几乎每隔百米就有一座。其中最为出名的十座桥,被编成了带谐音的“数字”童谣,它们是:一大木桥、二凰仪桥、三三脚桥、四螺蛳桥、五鲤鱼桥、六福禄桥、七蕺坊桥、八八字桥、九酒务桥、十日晖桥。今天随着城市发展变化,部分古桥已经消失或改建,变成马路或留下地名。如同母亲的人生在绍兴、上海、贵阳三地多次辗转后,只留下对故乡深深的念想。
雨落屋檐,炊烟袅袅,屋后河畔高高低低的捣衣声与乌篷船的桨声曾串起母亲儿时的梦。如今江南草长,杂花生树,时光蹉跎辗转,昔年在石桥上走过的足迹又在哪里?
此前,我与母亲一同回过绍兴。她说,古轩亭口荣禄春老字号饭店隔壁,民国时曾有一栋四层楼的民居,是我的外婆家。外公则住在今天荣禄春马路斜对面县前街的鲁迅电影院附近。
小时候,母亲住在外公家的老房子里,由她的爷爷奶奶养育,我的外婆每每从上海回乡,只住在荣禄春边上的四层楼房子里。母亲听闻便跑去看她,遥见一个女人凝脂雪肤,好看极了。再大一点,母亲每天去劳动路小学上课,都会途经周恩来祖居。夏天的时候,河水倒灌淹没街面,足足有同学们的大腿那么深。
因河而生的城市,防汛是头等大事。杭州湾潮水来势凶猛,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到浙东运河上各个时期的水利设施,记录了千百年来人们与水相生的故事。
在浙东运河博物馆,我们了解到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位于绍兴的山阴故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到西晋时,开挖西兴运河,此后与曹娥江以东运河形成西起钱塘江,东到东海的完整运河。南宋建都临安后,浙东运河成为当时重要的航运河道。
李白、杜甫、贺知章、王维、陆游、范成大、秦观、鲁迅……历史上,多少文人墨客取道浙东运河,又留下多少传世作品。这些都与运河上的碶闸和堰坝,以及运河所连结自然河流上的桥梁一起成为了今天重要的运河遗产。
除了汹涌的潮水,绍兴更有一池让人心泛涟漪的“镜水”。
唐朝大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中那句“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写的便是今天的绍兴鉴湖。那一年,86岁贺之章告老还乡。归家路上被孩童笑问客从何处来,这让离开家乡50多年的贺知章感慨万千。人生易老,世事沧桑,除了眼前这一池春水,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净尽了。
这次绍兴行,我第一次见到了贺知章笔下的镜湖水。春风中,湖水碧绿,两岸烟柳弄晴,船行湖面,徐徐而进,似在画中。确如王羲之所言:“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镜湖,又称鉴湖,位于绍兴市柯桥区。今天已成为内含东跨湖桥、快阁、三山、清水闸、柯岩、湖塘等景区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想要好好游览需花费一整天时间。到鉴湖游玩,少不了购买绍兴特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用鉴湖水酿造的绍兴黄酒。
出生于贵州,对于酒多少有些了解,我明白好酒的酿造必须有一个适合酿酒微生物综合协调生长的环境与气候。
绍兴黄酒属于低度酒,不但水分占80%,在糖化发酵等过程中,都需要水,所以水质好坏直接影响酒的酿造。而贵州冠绝天下的美酒——茅台,其酿造同样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要顺应季节变换,经历端午踩曲、重阳下沙、长期贮存等工艺环节的淬炼。
鉴湖之于绍兴黄酒,恰如赤水河之于贵州茅台。
如此一想,母亲的绍兴、我的贵州,尽管相隔1700多公里,竟然因这味蕾上的甘醇有了微妙的联结。“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眼前这一池镜湖水,亦在我心中泛起阵阵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