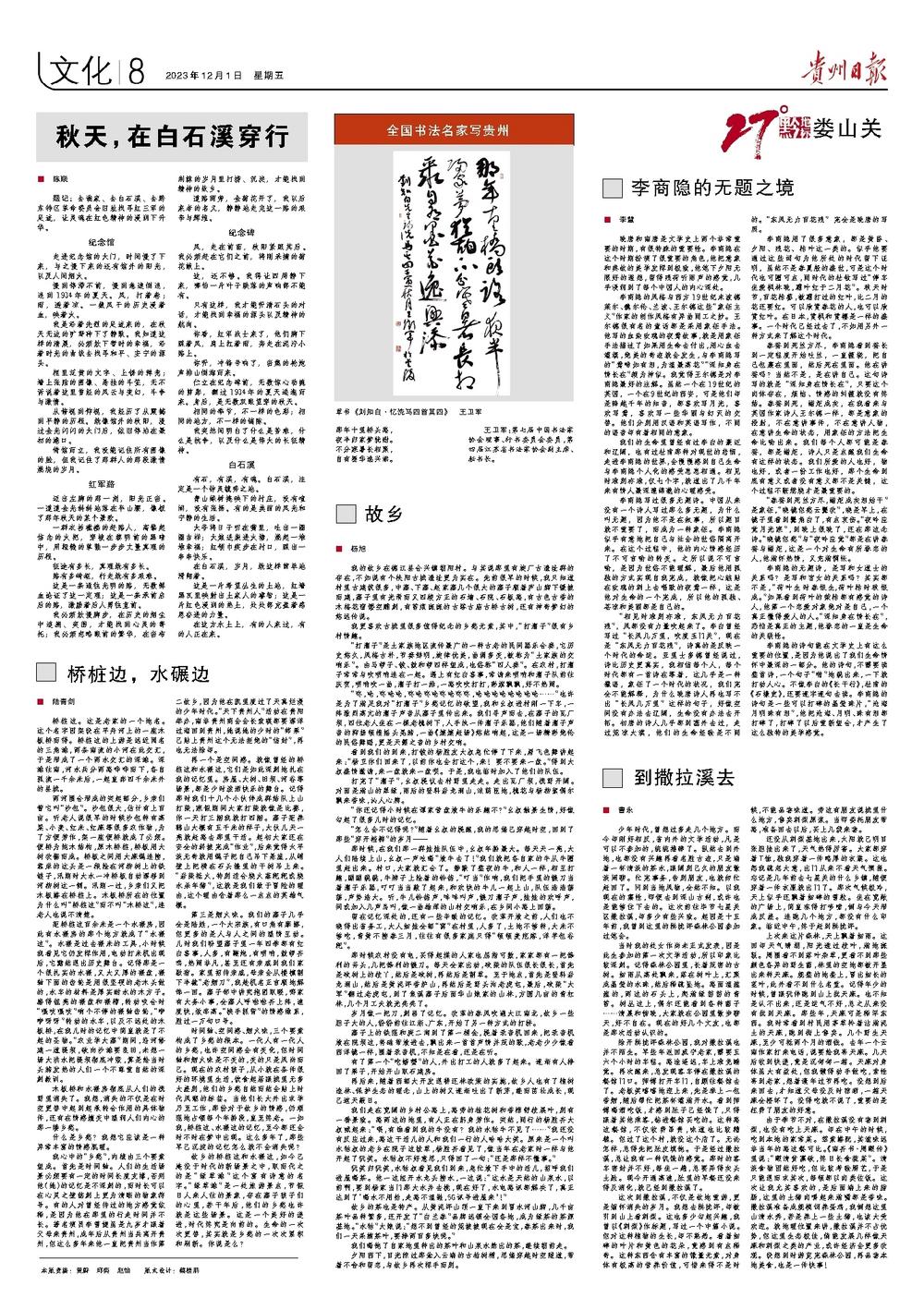■ 陆青剑
桥桩边。这是老家的一个地名。这个名字因架设在平舟河上的一座木板桥而得。桥桩边的上游是远近闻名的三角滩,两条南流的小河在此交汇,于是形成了一个两水交汇的深滩。深滩往南,河水兵分两路哗哗而下,各自孤流一千余米后,一起直奔四千余米外的县城。
两河围合形成的突起部分,乡亲们管它叫“沙包”。沙包很大,估计有上百亩。听老人说很早的时候沙包种有高粱、小麦、红米、红麻等很多农作物,为了方便劳作,架一座便桥就成了必须。便桥为纯木结构,原木桥桩,桥板用大树改锯而成。桥板之间用大麻绳连接,靠岸的这头是一根拴在河柳树上的铁链子,汛期时大水一冲桥板自动漂移到河柳树这一侧。汛期一过,乡亲们又把木板搭在桥桩上。木板桥所在的位置为什么叫“桥桩边”而不叫“木桥边”,连老人也说不清楚。
距桥桩边百余米是一个水碾房,因此有水碾房的那个地方就成了“水碾边”。水碾是过去碾米的工具,小时候我看见它仍发挥作用,电动打米机出现后,它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记得那是一个很扎实的水碾,又大又厚的碾盘,碾轴下面的齿轮是用很坚硬的老木头做的,水车的材料是厚实耐水的木方子。磨得锃亮的碾盘和碾槽,转动咬合时“嘎吱嘎吱”响个不停的碾轴齿轮,“咿咿呀呀”转动的水车,以及不远处的木板桥,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简直就是了不起的圣物。“农业学大寨”期间,沿河修建一道堤坝,欲向沙滩要良田,未想一场大洪水把堤坝彻底冲毁,算是给当时头脑发热的人们一个不尊重自然的深刻教训。
木板桥和水碾房彻底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想,消失的不仅是在时空更替中起到起承转合作用的具体物件,还有在情感嬗变中温润人们内心的那一缕乡愁。
什么是乡愁?我想它应该是一种异常丰富的情感肌理。
我心中的“乡愁”,内核由三个要素组成。首先是时间轴。人们的生活场景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支撑,否则他(她)的记忆是不深刻的,而时长可以在心灵之壁铭刻上更为清晰的物象符号。有的人对曾经待过的地方感觉依稀,是因为他在那里的行走时间并不长。著名演员李雪健虽是九岁才跟着父母来贵州,成年后从贵州当兵离开贵州,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贵州当作第二故乡,因为他在凯里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天下贵州人”活动在贵阳举办,南非贵州商会会长袁瑛都要漂洋过海回到贵州,她说她的少时的“邮票”已贴上贵州这个无法拒绝的“信封”,再也无法除却。
再一个是空间感。就像曾经的桥桩边和水碾边,它们是如此深刻地扎在我的记忆里。房屋、大树、田坝、河谷等场景,都是少时泼洒快乐的舞台。记得那时我们十几个小伙伴成群结队上山打柴,寒假期间大家打柴就像是比赛,你一天打三捆我就打四捆。寨子距养鹤山大概有五千米的样子,大伙儿天一亮就赶路去那里干活。起初大家还在安全的斜坡完成“作业”,后来觉得太平淡无奇就用绳子把自己吊下悬崖,从峭壁上把横在石头缝里的干树吊上来。“岩柴抵火,特别适合烧火蒸粑粑或烧水杀年猪”,这就是我们敢于冒险的理由,这个理由含着那么一点点的英雄气概。
第三是烟火味。我们的寨子几乎全是陆姓,一个大宗族,有口角有摩擦,但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互动。儿时我们盼望寨子里一年四季都有红白喜事,人多,有鞭炮,有唢呐,鼓锣齐鸣,热闹非凡,甚至还有亲戚到我们家歇宿。家里招待亲戚,母亲会从楼檩割下半截“老烟刀”,我趁机名正言顺地解馋一回。寨子邻中讲究抱团取暖,哪家有大务小事,全寨人呼啦啦齐上阵,速度快,效率高。“换手抓背”的情感维系,胜过一万句口号。
时间轴、空间感、烟火味,三个要素构成了乡愁的根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也许空间感会有变化,但时间轴和烟火味是不变的,变的只是风尚而已。现在的农村孩子,从小就在条件很好的环境里生活,饮食起居跟城里无多大差别,他们的乡愁自然而然会贴上时代风潮的标签。当他们长大外出求学乃至工作,那份对于故乡的情感,仍顽强地占领每个年龄段,直至终老。一如我,桥桩边、水碾边的记忆,至今都还会时不时在梦中出现。这么多年了,那些早已沉淀的记忆怎么就不会消失呢?
故乡的桥桩边和水碾边,如今已淹没于时代的新场景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绿草滩”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绿草滩”是一处旅游景点,节假日人来人往的景象,存在寨子孩子们的心里,若干年后,他们的乡愁也许就是这些场景。这是一个美好的递进,时代终究是向前的。生命的一次次更替,其实就是乡愁的一次次累积和刷新。你说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