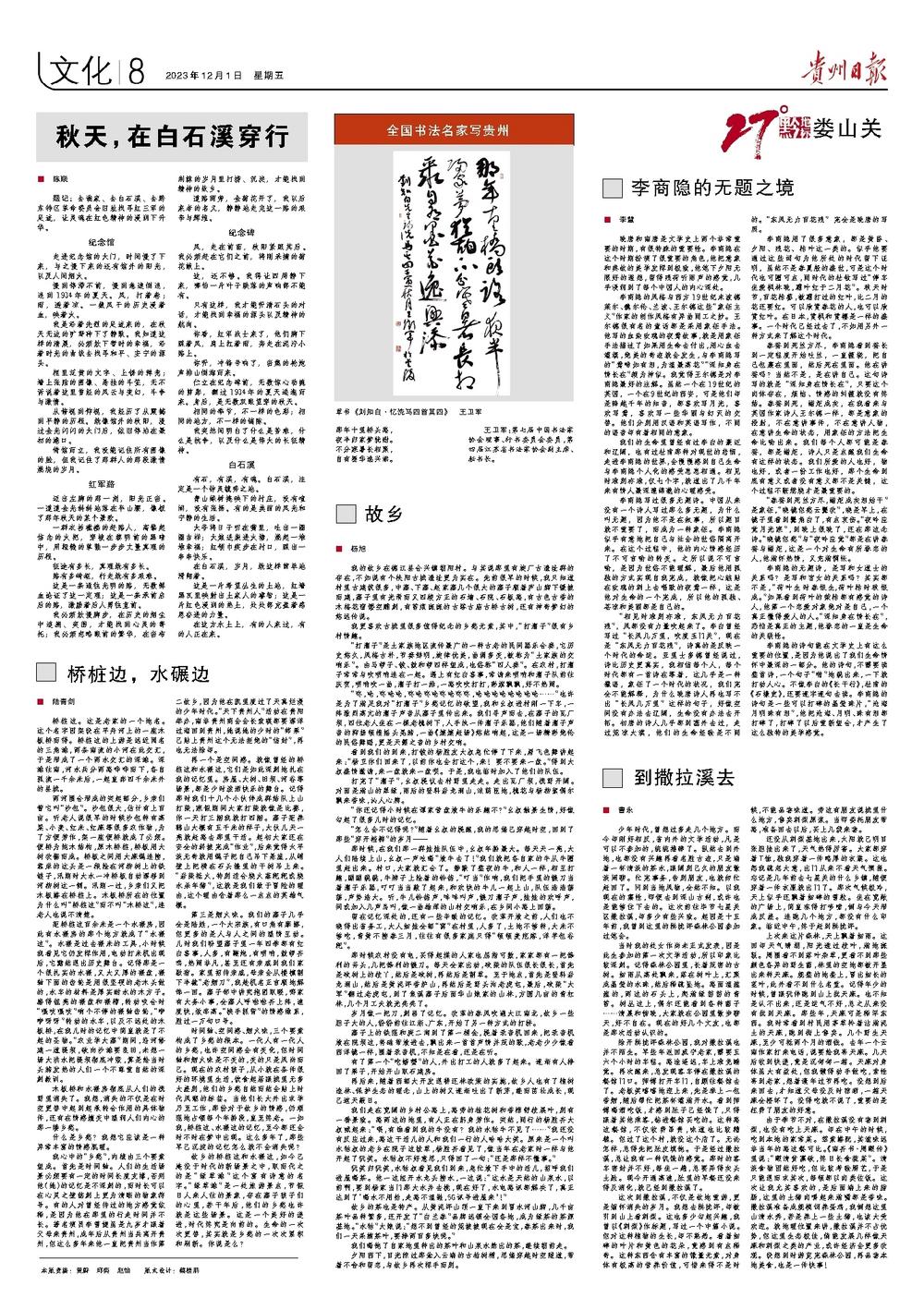■ 李慧
晚唐和南唐是文学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有很特殊的重要性。李商隐在这个时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把意象和典故的美学发挥到极致,他笔下夕阳无限好的遐想,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感觉,几乎浸润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李商隐的风格与西方19世纪末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王尔德这些“象征主义”作家的创作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尔德很有名的童话都是采用象征手法。他写的血染玫瑰的夜莺故事,就是用象征手法描述了如果用生命去付出,用心血去灌溉,绝美的奇迹就会发生,与李商隐写的“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深知身在情长在”颇为神似。我觉得王尔德是对李商隐最好的注解。虽然一个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在9世纪的西安,可是他们却是跨越千年的知音,都喜欢写月光,喜欢写莺,喜欢写一些华丽与幻灭的交替。他们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写作,不同的语音却有着相同的意象。
我们的生命里曾经有过李白的豪迈和辽阔,也有过杜甫那种对现世的悲悯,走进李商隐的世界,会慢慢感到自己生命与李商隐个人化的感受息息相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仅七个字,就道出了几千年来有情人最深邃绵邈的心理感受。
李商隐写过很多无题诗。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写过那么多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因为他不是在叙事,所以题目就不重要了,而成为一种象征。李商隐似乎有意地把自己与社会的世俗隔离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情感经历了不可言喻的转变。之所以说不可言喻,是因为世俗不能理解,最后他用孤独的方式实现自我完成,就像把心脏贴在玫瑰的刺上去唱歌的夜莺一样,这是他对生命的一个完成,所以他的孤独、苍凉和美丽都是自己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风都没有力量吹起来了。李白曾经写过“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现在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诗真的是反映一个时代的命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我相信每个人,每个时代都有一首诗在等着,这几乎是一种谶语,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状况,我们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晚唐诗人再也写不出“长风几万里”这样的句子,好像空间没有办法去辽阔,生命没有办法去开拓。初唐的诗人几乎都到塞外去过,走过荒凉大漠,他们的生命经验是不同的。“东风无力百花残”完全是晚唐的写照。
李商隐用了很多意象,都是黄昏、夕阳、残花、枯叶这一类的。似乎他要通过这些词句为他所处的时代留下证明,虽然不是春夏般的盛世,可是这个时代也可圈可点,同时代的杜牧写过“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天时节,百花枯萎,被霜打过的红叶,比二月的花还要红。可以欣赏春花的人,也可以欣赏红叶。在日本,赏枫和赏樱是一样的盛事。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了解这个时代。
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看到蚕长到一定程度开始吐丝,一直缠绕,把自己包裹在里面,然后死在里面。他在讲蚕吗?当然不是,是在讲自己。这句诗写的就是“深知身在情长在”,只要这个肉体存在,烦恼、情感的纠缠就没有终结。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在我看来与英国作家诗人王尔德一样,都是意象的投射,不在意讲事件,不在意讲人物,在意讲生命的状态,用象征的方法把生命比喻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春蚕,都是蜡炬,诗人只是点醒我们生命有这样的状态。我们所爱的人也好,物也好,或者一份工作也好,那个生命到底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都不是关键,这个过程不断燃烧才是最重要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象征,“晓镜但愁云鬓改”,晓是早上,在镜子里看到鬓角白了,有点哀伤。“夜吟应觉月光寒”,到晚上很晚了,还在那边念诗。“晓镜但愁”与“夜吟应觉”都是在讲春蚕与蜡炬,这是一个对生命有所眷恋的人,他满怀热情,又充满惆怅。
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写和女道士的关系吗?是写和宫女的关系吗?其实都不是,“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如果看到荷叶的荣枯都有感觉的诗人,他第一个恋爱对象绝对是自己,一个真正懂得爱人的人。“深知身在情长在”,恐怕是真正的主题,他眷恋的一直是生命的关联性。
李商隐的诗句能在文学史上有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生命情怀中最深的一部分。他的诗句,不需要读整首诗,一个句子“啪”地跳出来,一下就打动人心。不像李白的《长干行》,杜甫的《石壕吏》,还要逐字逐句去读。李商隐的诗句是一些可以打碎的晶莹珠片,“沧海月明珠有泪”,他把沧海、月明、珠有泪都打碎了,打碎了以后重新组合,才产生了这么独特的美学感觉。